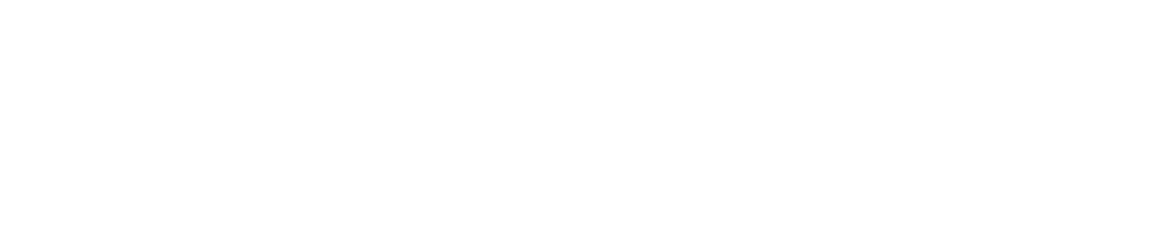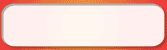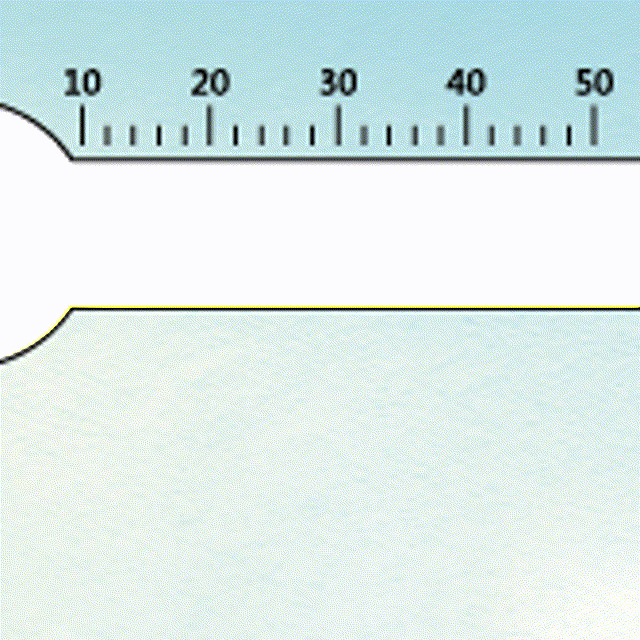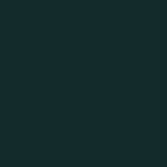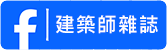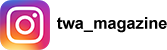10
逢甲共善樓與淨零時代的新包浩斯運動 一個時代精神詮釋的考察
Virtuosi Hall at Feng Chia University and the New Bauhaus Movement in the Net-Zero Era –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Zeitgeist
/ By Tseng, Tse-Fong
逢甲共善樓的誕生與爭議
一個時代事件的序曲
臺中的午後,陽光從水湳中央公園斜灑進逢甲大學新東校門,一棟壓低體量、細節繁複的建築映入眼簾。草坡延伸至屋頂,木格柵如呼吸般篩散光影,大片玻璃模糊了內外的界線。這就是近期在臺灣建築界引發最多議論的「共善樓」。
第一眼的感受,既顛覆又吸睛。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大學建築的嚴謹方格,反而像是一塊由風、流動的人群與自然共同雕刻的地形。兩層低矮的量體,配合N型軸線,串連層層外廊與穿透庭院。斜坡、穿堂、中庭、綠意庭園交織出一種導引移動的節奏。室內透過玻璃帷幕一覽無遺,大講堂、演藝廳、多媒體教室與跨域交流空間,都像被納入一張可自由穿透的網絡。這不是封閉的盒子,而是一個由格柵、坡道與光影織構的開放場域。
在校方的文本裡,共善樓被賦予「沉浸式學習、公共文化與開放校園」的承諾,以「共善大好、春風化雨」的價值敘事回應社會期待。這樣的語言很容易讓人信服,也讓人看見逢甲大學試圖以建築來體現治理願景與理想。
另一個鮮明印象,來自新校地「公園般」的氛圍。低矮量體與覆滿草皮的屋頂,與周邊庭院連成一片,宛如校園退隱於自然的生態島。這讓人自然聯想到當代城市最受關注的課題-Urban with Nature。這裡不僅傳達淨零、韌性與氣候中和的理想,更改寫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日常關係。隈研吾將其命名為臺灣首座「地景建築」,呼應他一貫的「負建築」哲學:讓建築退隱、消失,追求共生。
文/曾梓峰(逢甲大學特聘客座教授)
圖片提供/逢甲大學